罗氏、辉瑞急刹车,AZ、GSK逆势加码,全球营收TOP20 H1钱都砸哪儿了?
还会MNC 押注新一轮“大BD/并购”吗?
如果只看2025年上半年的BD热潮,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但进入中报季后,来自全球巨头们的信号又多了几分不确定。
整体来看,2025年H1财报,全球药企研发投入占营收比普遍“收缩”,TOP20中逾半数下调研投占比,BMS大幅削减,罗氏连续三年下行,吉利德密集裁撤管线止损。行业的隐形共识正在从押注增长切换向守住效率,并购似乎也由动辄百亿的大单,转向更可控的多笔小单。
但收缩并非停摆。GSK、再生元与阿斯利康仍在减法周期中做加法:GSK成为研发增量第一,再生元研投占营收比领跑,AZ以约24%高位投入依旧交出双位数增长。三者共同特点是把有限增量集中到明确里程碑上,追求更高的研发效率,增厚护城河。
可以预见的是,当营收增速放缓,研投占比走向分水岭,2025年下半年也将走到MNC格局洗牌的临界点。
(数据来源:Wind)
回撤潮
时间来到2025年年中,跨国药企的研发策略发生了近乎180°的转向。两年前,无论是凭借抗病毒药/疫苗“躺赢”的阵营,还是寄望以大手笔研发投入扭转基本面的阵营,虽也会“砍管线”,但总体是边砍边加、持续抬高研发强度。到了今年中报,保守、收缩成了更高频的关键词:研发/营收占比超过30%的MNC从两三家锐减到几乎仅剩再生元坚守;TOP20里有8家下调研发投入,BMS削减幅度最大,约7.6亿美元。
最具代表性的是辉瑞。2025年H1营收283.67亿美元、研发投入46.85亿美元,占比17.77%。更具象的“回撤”出现在赛道选择上:在2023年与2025年相继叫停两款,口服GLP-1接连受挫后,辉瑞在发布H1财报同期,宣布终止了最后一款GLP-1管线PF-06954522。代谢领域的另一核心项目——GIPR拮抗剂PF-07976016也因联用伙伴Danuglipron被叫停而前景受挫。多轮打击后,管理层在Q2电话会上释放出更保守的信号:代谢、肿瘤、疫苗仍是重点,但将以多笔小型交易构建管线,肥胖领域并购“会非常谨慎,不会付出过高溢价,只为资产应得的价值”。
同样典型回撤的还有罗氏,伴随其在7月底发布H1财报,两项大消息几乎“带崩”全球研发界。
一则是,其TIGIT管线RG6058(tiragolumab)仅存的两项III期试验正式终止——在被视为“下一个PD-1”的靶点上,这意味着,最能抗、坚守最久的玩家也撤退了。
另一则是,罗氏旗下基因泰克与Bicycle Therapeutics基于双环肽平台的17亿美元级合作亦告终止。Bicycle随后宣布裁员约25%,配合总费用下调30%,以将现金流续至2028年。
此外,由于罗氏大手笔的“砍项目”,其今年上半年研发费用率为19.63%,这也是罗氏的H1研发费用率连续三年下滑。
在适应证层面宣告“阶段性终结”的还有吉利德。2019年,吉利德布局NASH的核心管线selonsertib的研发遭遇滑铁卢,由于关键临床试验未达预期,让本在全球NASH药物开发上领先的吉利德,倒退了一大截,也让吉利德与全球NASH领导者的目标失之交臂。不过,之后与诺和诺德司美格鲁肽的合作,让吉利德再次燃起希望。其两款药物cilofexor、firsocostat与司美格鲁肽初步合作的积极数据,让两家公司不断加深合作。
然而,当时间来到2025年,这个梦想再次破碎,伴随吉利德发布H1财报,上述两款药物被列入了终止名单,这不仅意味着吉利德与诺和诺德的分手,也预示着吉利德想要在MASH领域分一杯羹,也宣告中场暂停。
不过,吉利德并未因MASH适应证研发折戟,就削减研发投入,2025年H1,仍然高达28.7亿美元,占137.49亿美元营收比例高达20.87%,在营收TOP20的MNC中仍然是佼佼者。
总而言之,从狂增研发转向保守投入,从重仓大项目到多笔小型投入的组合拳,或许会在2025年年中成为MNC管线布局未来的新常态。
谁在“减法周期”做加法
即使“收缩”成了跨国药企研发投入的高频词,但也可以看到,仍有少数玩家逆势加码,把有限的资源精确投向有明确里程碑的管线上。GSK、再生元与AZ正是这波加码的主角。
即使在2025年H1,GSK的营收依然未能回归TOP10阵营,但在抗肿瘤领域的持续增长,还是给这家公司带来了进一步深耕的信心。营收层面来看,GSK上半年总收入约为155.02亿英镑,同比增长达5%。增长的两极非常明确:呼吸、免疫与炎症(RI&I)收入17.67亿英镑,同比+18%;肿瘤收入8.99亿英镑,同比+47%。
也正因如此,可以明显看到,GSK也将研发火力集中于这两大业务上,全管线60余项在研临床资产、16项处后期,年内已拿下3项FDA批准,还将再点火4个关键研究。
RI&I端,一边是Nucala获得COPD适应证,另一边是超长效IL-5抗体depemokimab治疗哮喘/鼻息肉即将在12月16日迎来PDUFA;肿瘤端,则以ADC为核心,B7-H3ADC就是年内关键研究之一,B7-H4ADC预计明年初启动。GSK的逻辑很清晰:用稳定的RI&I构筑“底盘”,用肿瘤ADC带来“弹性”,研发节奏围绕“后期兑现+平台复用”展开,从而解释了为何它在TOP20中呈现出最明显的研发增量。
GSK是研发投入增长最多的公司,再生元则是研投/总营收比增长最快的公司。再生元2025年H1总收入67.04亿美元,研发投入总额27.71亿美元,研投率攀至41.34%;其中,Q2单季研发费用同比增加19%,直接对应中后期项目的密集节点。
不过,也能看出,再生元在急于寻找阿柏西普的继任者。一方面,公司加速“肿瘤双引擎”:巩固Lynozyfic(linvoseltamab)在复发难治多发性骨髓瘤上的地位,推动Libtayo术后CSCC的潜在获批;另一方面,在炎症与呼吸领域持续扩展Dupixent适应证,同时评估Itepekimab在COPD赛道的差异化位点。第三条主线落在代谢赛道:在引进双GLP-1/GIP之后,叠加自家“肌肉维持”抗体开展组合研究,把“减重质量”(在降低脂肪的同时保住瘦体重)作为下一代竞争点。
另一大看点其实是阿斯利康,作为TOP10中还能保持10%左右增长少数几家公司之一,AZ其实面临的专利悬崖风险也相对较远,但其仍然选择保持高研发投入来押注新管线。其H1财报显示,AZ上半年总营收约280.45亿美元,研发投入67.07亿美元,同比增加16%,研投占比约24%。
拉动这波投入的,是肿瘤、呼吸免疫与CVRM三条战线几乎同步的“临门冲刺”:肿瘤方面,Tagrisso、Imfinzi、Datroway与Enhertu的新适应证与里程碑密集推进;呼吸免疫方面,Breztri两项哮喘适应证进展喜人,Fasenra与Saphnelo取得积极信号;CVRM方面,baxdrostat在临床研究达到主要终点。更关键的是,AZ把增量押在最接近商业兑现的中后期资产,同时前置布局自体细胞疗法、口服代谢组合与核药等新疗法上,力争新增长点。
把三家“逆行者”放在同一维度里,能看到共性与差异化:共性在于都把研发增量具有明确里程碑的管线上,并以BD补齐短板;分歧在于路径选择,GSK押注两极驱动,用RI&I稳住基本盘、靠ADC提升弹性;再生元保持高研投加速多赛道新引擎,试图对冲单品更替;AZ则以密集里程碑+平台押注的打通中短期与中长期增长。
作者:访客本文地址:https://lrpm.cn/?id=18663发布于 2025-08-19 15:15:45
文章转载或复制请以超链接形式并注明出处青团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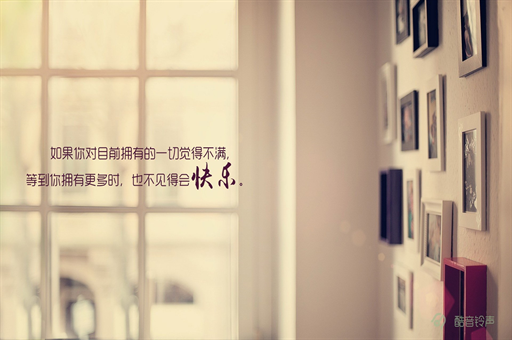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