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的人设陷阱与钟的网暴反思
17个月前,宗庆后先生去世,他被普遍认为是中国最后一位工人企业家,举国缅怀。他生前所创办的娃哈哈集团与同城钟睒睒先生所创办的农夫山泉集团虽长期是最主要竞争对手,但两位企业家与两家企业之间都恪守君子之道。我记忆中两家企业与两位企业家之间在过去的至少20几年间都从未针对对方发起过拙劣的舆论攻击,这是很罕见的。
遗憾的是,在宗庆后先生去世之后的至少半年,一场策划痕迹明显的网暴顺水推舟的发生了。在宗先生的道德标尺下,钟睒睒家族被无端审判,其“儿子拥有美国国籍”成为网暴者攻击的焦点。
如今,17个月过去,当宗先生因子女遗产纠纷之事戏剧性地遭受道德质疑时,公众似乎又开始反思自己迷惑于人设陷阱。
这篇文章我们无意讨论公众情绪的非理性化,如《乌合之众》一书的观点,群体具有非理性、易受暗示和冲动的特征,这并非社会发展阶段所能扭转。
但是,我们想思考一个问题,即当下中国商业社会对企业家的“模范期待”正如何陷入一个制度性误区:我们一边是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企业家,一边却理所当然地用最严苛的道德尺度去捆绑他们。
壹
首先,对过去一年多的往事做简单回溯。宗庆后和钟睒睒,皆为一代企业家,但两人的商业风格与家族治理选择迥异。宗以“极简生活”“亲自巡店”闻名,钟则低调寡言。宗先生坚持“娃哈哈不上市”,而农夫山泉是一家市值数千亿的上市公司,钟先生一度稳居首富,他的财富可以轻易被量化。
于是,宗庆后去世之后,网络舆论开始发起一场“人设对比游戏”:一个是“把女儿留在身边、身体力行坚守民族产业”,一个是“儿子为美国籍、深居幕后躲避质询”,孰为爱国,孰为背叛,仿佛不言自明。
但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这种逻辑本身是对企业家角色的误解。
我们想首先应明确企业家的公共价值,我将其主要定义在“公德”维度——即其是否推动就业、促进经济发展、尊重契约、引领技术与品牌进步;而非“私德”层面的道德完人。
娃哈哈与农夫山泉,宗先生与钟先生,在这一点上都是最为杰出企业与企业家。两家企业都在全国提供了数以十万计的就业岗位、为数以十万、百万计的家庭提供收入;他们的产品与构建的商业体系为全社会增加了福祉,这都是社会不可否认的公共贡献。
在“公德”之外,才是“私德”。宗先生的家族结构,子女国籍与财富安排,以及他的生活往事等等,都是私德范畴;同样,钟睒睒儿子是否持美国国籍,他本人有怎样的生活物质偏好。
以上私德种种,本质都是一个家庭治理结构问题。比如,子女财富安排,子女国籍等等甚至可视为企业传承的一种防火墙设计,而非爱国与否的道德判断。
现实是,中国最优秀的企业家的后代都在进行全球化布局,多国资产配置再普遍不过。即便是企业本身,其持股架构亦非中国本土。若将企业家的子女国籍问题等同于“是否忠于国家”,则是对现代企业治理基本原则的曲解。
如果以上述由头对企业家发起网络暴力,用民族主义情绪裹挟对企业家的道德进行指责,这既非正义表达,也完全脱离事实本身。
企业家不是公共道德的替罪羊。我们不能在鼓励创新、呼唤企业家精神的同时,又用圣徒标准检验他们的每一个“私德”决定,期待他们在公德与私德上皆完美无瑕,不仅是对其人性的误解,也是对他们社会贡献的扭曲,这不是法治社会的逻辑,更不是成熟市场的规范。
贰
宗先生之所以在身后赢得如此多的情感投射,并非偶然。他是一个“符合时代需要”的符号:草根出身、廉洁朴素、对子女严厉、坚决不海外扩张。这些标签在特定语境下,被放大为某种“民族企业家”的精神图腾。
很多时候,相当多数的企业家也沉迷于享受被公众施加的此类精神图腾,有一些甚至主动营造自己的图腾。这就决定了他们必须竭力避免自己的私德破坏这种图腾,进而一步步小心翼翼地打造自己的人设,为自己埋下人设陷阱。
三个月前,小米汽车发生致命车祸致三位女孩死亡的事件后,雷军先生也陷入被汹涌网络的暴力讨伐中。我当时撰写过一小段文字发布在朋友圈,摘录如下:
“中国企业界喜欢造宗教、造神,希望借此把自己和企业推到超凡地位,而神和宗教最大特点就是不能有瑕疵的和阴暗面的。Jack Ma成功尝试过,雷军正在尝试,一个在顺周期时代,一个在逆周期时代。逆周期时代更需要神,所以造神会更快、更疯狂。
经历过大繁荣时代的日本、美国企业界在历史上也曾喜欢造神,比如,松下幸之助、福特和洛克菲勒等,有集体主义造神,也有市场造神。
从趋利因素看,消费和科技行业的宗教化有几何效应。但如果实在要造神,把他不完美的一面暴露出来并不是坏事,群体性无信仰社会的特点就是容得下不完美的神。”
企业家的“完美人设”从来都是不完整的,更不是公众看到的全部。实际上,在宗先生去世不到一个月后,就已经有媒体曝出其身后遗产陷入纠纷,三名非婚生子女申请争夺18亿美元的信托资产。宗先生非婚子女的存在实际上是相当范围所知的非新鲜事。
在改开40多年里,这种复杂、纠结、家庭关系模糊的结构,恰恰是许多第一代企业家未能妥善处理的“私德雷区”。
这并非宗先生一人之罕见之事,在中国的第一代企业家中,几乎普遍存在“家族治理未设机制”“企业产权与家事纠缠不清”“企业传承倚重长子嫡系”等类似问题。
在这种结构下,企业家的人设往往变成一种集体投射:我们希望他们完美,所以他们必须完美。而一旦出现裂痕,如子女移民、婚姻不忠、投资失误——这种完美人设就会反噬回去,形成“背叛民族”“不负责任”“资本家本性暴露”等激进指控。
特别是“国籍问题”,几乎成了压倒性的道德鞭子。问题在于,企业家子女的全球身份布局,在现代企业治理中早已是常态。今天的现代化企业必须应对跨国税务、全球化教育、法律风控等议题,子女入籍只是结构设计的一部分,不能等同于政治背叛。
宗先生的人设之所以难以复制,正是因为他是特定时代的产物。而用这一人设去否定其他路径的成功者,不仅不公,也在扼杀多元企业路径的正常发展。
同样,以此类事务,去发起类似于对钟睒睒先生一样的网暴,则是完全不可理喻,也是商业文明与法治社会的倒退。
叁
行文至此,我们不妨再谈一谈娃哈哈的当下继承者宗馥莉女士。对宗女士在宗先生去世后所面临的局面,我们此前已撰写《宗馥莉的艰难险阻》有过阶段性铺就。
宗馥莉女士在宗先生生前就已多次站在台前,她是公众所默认的企业继承者。但是,从宗馥莉上位一年多以来的表现看,她并未展现出稳定治理者应有的稳重与理性,反而频频陷入“意气操作”与“权力内斗”的漩涡。
首先是对合作伙伴今麦郎事件的处理。今年初,娃哈哈突然终止了与今麦郎的一项代工协议,引发舆论哗然。双方曾合作多年,在饮用水包装、渠道共享等方面有深度捆绑,今麦郎也在不少区域为娃哈哈提供关键供应支撑。如果说解约行为是正常的商业决策,那么公开指责对方的质量问题,则暴露出宗馥莉在维护长期商业合作关系方面的短视。
其次是宗馥莉的“辞职威胁”事件。在父亲去世短短几个月后,她即公开以全员函件的形式,仅以部分股东对其经营管理提出合理性质疑,就公开声称要辞去总经理等所有职务。在短短时间后,又撤回辞职要求。
当然,她还有更多流传于民间的更为情绪化的发言,作为企业一号位,尤其是在其父亲去世,企业亟需稳定局面之时,以这种消极态度应对,加剧的不仅仅是内部不安,更是对这家企业上下游,尤其是对娃哈哈经销商渠道体系的稳定性造成动荡。
更为严重的是近期曝出的“关闭工厂事件”。娃哈哈在多个省份进行人事调整,并同步关闭数家区域工厂。外界提出的质疑是,这背后是否并非市场因素,而是宗馥莉试图削弱同父异母弟妹控制的区域资源。
一家企业的治理权,尤其是如娃哈哈这类国有资本作为大股东的大型企业,其最终责任是对所有股东、员工、消费者负责,而不是为家族内斗服务。
若家族伦理绑架企业决策,企业必将失去其最基本的商业理性。
遗憾的是,当网络公众仍沉迷于“民族企业家”叙事时,极少有人看到:宗馥莉继承的,不仅是一个辉煌品牌,还是一个没有防火墙、没有建成成熟的现代化企业治理制度的“遗产雷场”。
而在上述问题的解决上,宗馥莉要打的仗,恐怕远比争夺家族遗产分配之事要繁重得多。
最后
今天,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企业家。不是完人,而是制度意义上的企业家。他们的价值,不是建立在人设神话或民族叙事之上,而是以公共理性、市场规则、契约精神为支撑的企业行为。
如果我们不能走出“模范企业家”的人设陷阱,就会反复陷入“神化—幻灭—围剿”的社会情绪轮回中。
作者:访客本文地址:https://lrpm.cn/?id=14949发布于 2025-07-15 15:12:41
文章转载或复制请以超链接形式并注明出处青团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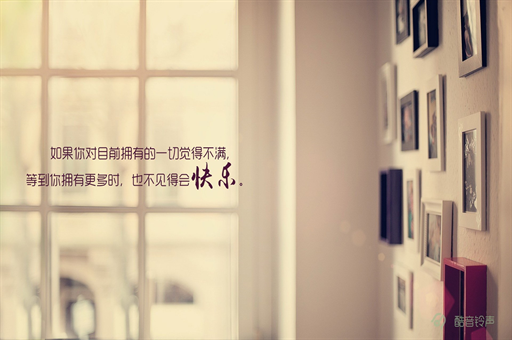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